斯坦利被遗忘的记录
1906年5月10日的伦敦,弥留之际的亨利·斯坦利(Henry Stanley)躺在病床上,回忆着自己的一生。或许他想的是在刚果河流域为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开疆拓土,抑或是在坦噶尼喀湖边乌吉吉的那句“我想您就是利文斯通博士?”若都不是,那么就有可能是自己在穆特萨国王的领地遇到四个来自甘巴拉嘎拉山(Mount Gambaragara)的白皮肤非洲人的故事。
斯坦利与甘巴拉嘎拉山的奇遇曾经大量出现在他的日记、现场快报、新闻稿件、探险记和自传中,甚至在他自己的悼词中这一部分也没有缺席。然而,人们对斯坦利的探险记的关注,大多把重点放在了南部非洲的地理发现,以及探险过程中所付出的人命代价。因此直到近年,有关斯坦利的传记很少谈到甘巴拉嘎拉山,更不要说他在山下遇到白色部落的故事。理查德·霍尔在1975年出版的《斯坦利传》(Richard Hall, Stanley: an Adventurer Explored, Purnell; BC ed ,1974)中对这段奇遇的描述只不过寥寥数行。而詹姆斯·纽曼在自认为重现斯坦利每一趟探险的来龙去脉的《帝国足迹》(James L. Newman, Imperial Footprints: Henry Morton Stanley's African Journeys, Brassey's, 2004)一书中,甚至对这段奇遇只字未提。
不过在斯坦利发现了甘巴拉嘎拉山白人部落后不久,欧美学界却掀起了一股在全世界寻找白人部落的浪潮。这一时期大量的探险报告,猎奇小说层出不穷,一直持续到了二战之前。只是这股浪潮在现代科学的研究中逐渐被证伪与遗忘,渐渐并不被现代人所知。然而,这场已经被忘却的寻找白人部落的运动,却直至今日仍对世界产生了潜在的影响。迈克尔·罗宾森的《非洲失落的白色部落:探险家、科学家与一段改变人类命运的假说》(Michael F. Robinson, The Lost White Tribe:Explorers, Scientists, and the Theory that Changed a Contin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便是对这场运动进行探究的一部着作。该书英文版于2016年于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而台湾的猫头鹰出版则于2018年5月出版了其繁体中文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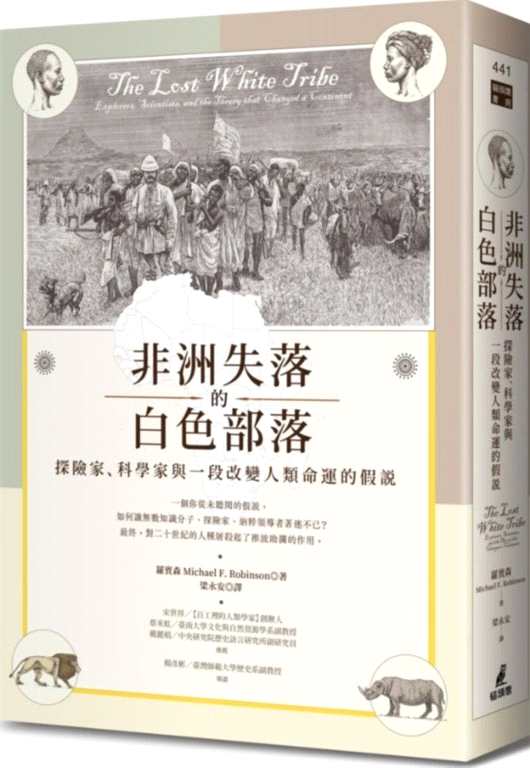
迈克尔·罗宾森是美国哈特福德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领域为“探险”在科学与文化领域中的角色。其作品《最冷的大熔炉:北极探险与美国文化》(Michael F. Robinson, The Coldest Crucible: Arctic Exploration and American Cultur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荣获了2008年“美国科学史论坛奖”。为了写作这本《非洲失落的白色部落》,罗宾森不但在欧美非三大洲各图书馆检阅19世纪后半叶以来的各种与探险相关的史料,甚至还寻着斯坦利的探险路线,亲身赶赴甘巴拉嘎拉山下,望着这座赤道上的雪山闪烁的耀眼光芒,体会当年斯坦利内心的深处所想:这白色部落到底从何而来?
非洲内陆存在着白人部落?
自上古时代以来,欧洲人就开始了与非洲的种种接触,例如希腊人始终与隔海相望的埃及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往来。在通过埃及与希腊进行的欧非贸易中,很多如象牙之类商品并不产自地中海边的埃及,而是通过尼罗河由非洲内陆运向埃及。因此,通过埃及,欧洲人一直对非洲内陆保持着关注。不过这种关注却一直是零零散散,并没有一个对非洲内陆较为完整的认识。所以,在欧洲一直流传着对非洲内陆的种种奇怪传说,比如非洲内陆生活着狗脸人,以及在尼罗河源头附近存在着赤道雪山。

尼罗河源头
当然,欧洲人对非洲内陆的认识也并非都是传闻,例如非洲内陆居住着很多黑人部落,以及乞力马扎罗山的存在。但随着欧洲人对非洲内陆的认识逐渐增加,却也发现了一些超出自己常识的状况出现,比如在非洲内陆其实也生活着白皮肤的非洲人。
关于非洲内陆生活着白皮肤群落的传说由来已久。在托勒密(Ptolemaeus)绘制的世界地图中,就把“白色的埃塞俄比亚人”放在了非洲内陆,不过他对“白色的埃塞俄比亚人”并没有体质特征等方面的详细描述。而较早对非洲内陆白皮肤群落有详尽描述的是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老普林尼在《自然史》(Naturalis Historia)中曾经提到,在非洲内陆往南越过撒哈拉沙漠后,住着一些“白色的埃塞俄比亚人”。这些“白色的埃塞俄比亚人”挖洞而居,体毛浓密,牙齿尖锐,没有语言,以刺耳的、类似口哨的声音来沟通;有着海蓝色的眼睛,夜间视力也极好,并且从小有着金色或白色的头发。到了查士丁尼时代,普罗科匹厄斯(Procopius)在《战争史》(History of the Wars)一书中也提到在沙漠以南,存在着身体非常白,金色头发的族群。
随着欧洲人对非洲内陆的了解逐渐深入,类似的超出自己“常识”的事情也变得越来越多,使得欧洲人开始对非洲土着的观感发生了变化:非洲内陆的部落是否和自己有着共同的祖先?如果是的话,他们是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会到非洲去?在这个过程中,又是什么原因让他们的外观变得如此和自己不一样?如果按照这样解释的话,就需要重新建构一套无法通过直接观察得到的历史,而将目光转向一些必须靠想象力才能唤起的事件与传说。由此,才可以解释了为何一支族群才可以从他们的原居地迁移到遥远的现居地。
这种想法其实反映了文艺复兴时代前,在基督教文化中探索人类起源的过程中,血缘系谱的重要地位。这一时期的欧洲人,希望将非洲人也纳入到人类起源的系谱之中。而对这种血缘系谱的探求,追根溯源,便来到了《圣经》的记载中。
《圣经》中的“含族诅咒(the curse of Ham)”
在《圣经》的记载中,所有的人类都是亚当与夏娃的后代。但后来因为人类作恶多端,上帝降下大洪水以毁灭人类。不过因为诺亚多行善事,于是上帝让诺亚建造方舟避难。大洪水过后,人类便剩下诺亚一家存活。后来,诺亚的后代在地球上逐渐繁衍,并不断迁徙,因此如今的人类都是诺亚的后代。
诺亚有三个孩子:闪、含、雅弗。在大洪水过后的,《圣经》的《创世纪》中记载了一个故事:一天诺亚喝醉了酒,脱光了衣服躺在帐篷里,含看到自己的父亲赤身裸体躺在帐篷里,就出去告诉他的两个兄弟。这时候闪和雅弗拿了一件长袍,搭在两人的背上,倒退着走进帐篷,把长袍盖在了父亲身上;他们把脸转向外面,没有看到父亲的裸体。诺亚酒醒后,知道了三个孩子所做的事情,便说要含以及含的后代做两位兄弟及其后代的奴隶。
虽然《创世纪》中诺亚的这个诅咒是为《出埃及记》中摩西带领犹太人出埃及统治迦南的铺垫(因为在《创世纪》记载的谱系中,“迦南”是含的孩子),但就后世的神学家而言,其对诺亚的这一诅咒便有了不同的解释。随着四世纪奴隶贸易的兴起,神学家们便将这一诅咒视为黑人拥有黑皮肤以及黑人受到奴役的原因。随着欧洲人的足迹不断遍布全球,大量超出欧洲人“常识”的族群也不断被发现,因此这一诅咒也开始不断被用来解释落后族群和这些族群被奴役的理由,究其原因在于这些族群也不断被整合入《圣经》的记载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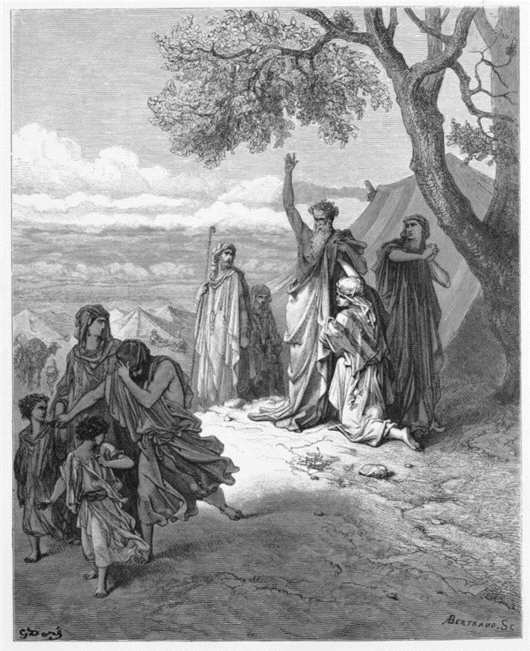
含的诅咒
到了十八世纪后半叶,随着实证主义的兴起,这种“含族假说”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一批博物学家通过比较语言学与头骨测量学,认为人类的起源应该是多元发生的。他们认为,《创世纪》中记载的人类起源故事,只讲述了高加索人的起源,并没有延及其他的人种,因此亚当和夏娃也只是高加索人的祖先,诺亚的故事也只是一度近乎灭绝后来又重新繁衍起来的高加索人种的故事。故而“含的后代”也是高加索人而并非黑人。与《创世纪》中记载的高加索人的产生同时,其他大陆上也产生了相应的人种,非洲自然也不例外。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含的后代”的一支入侵非洲并建立统治,又与当地的土着通婚,因而形成了如今的非洲种族。又因为“含的子孙”被诅咒,所以非洲是注定落后于欧洲的。因此在非洲的看似“先进”的发现,如南部非洲的“大津巴布韦”,必定不是非洲人所创造的,其创造者一定是此前到来的白人。
当来自欧洲的传教士将“含族假说”传入非洲之后,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当斯坦利找到利文斯通后,便进入了维多利亚湖畔布干达王国的领地。当斯坦利与布干达的穆特萨国王(Muteesa I Mukaabya Walugembe Kayiira)谈起《创世纪》时,斯坦利发现身居非洲内陆的穆特萨国王对《创世纪》,尤其是“含的后代”进入非洲的说法了如指掌。因为在非洲内陆的很多部落,尤其是有关布干达王室起源的传说中,经常会提到来自北方的神秘白人。这些神秘白人经过种种考验击败了本地的土着,最终成为了本地的王的祖先。穆特萨国王利用“含族假说”建立了与欧洲传教士势力的联系,也以此强化了自身统治的合法性。也因为如此,使得以斯坦利为代表的欧洲探险家们,更加相信在非洲内陆,并不仅仅是存在零星的白皮肤非洲人,更可能存在着一个尚未被发现的白人群落。

斯坦利遇到利文斯通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后期,非洲内陆存在未知白人群落的传说,开始走出探险家们的世界,进入了通俗文学领域。以亨利·哈葛德(Henry Haggard)的探险小说《所罗门王的宝藏》(King Solomon's Mines)为代表,展现了欧洲的探险家们非常偶然的在非洲内陆深处发现了隐居已久的白人群落的故事。在一系列的故事中,白人群落并不一定是含的后代,也有可能是例如早期的腓尼基探险家、迷失的十字军,甚至早期到达非洲但与欧洲本土失去联系的传教士的后裔。这些白人群落与世隔绝,因此仍旧保留了很多在工业化时代已经消失不见的古老美德。小说的主人公们也因发现了这些古老美德使自己的内心达到了救赎。而这种对“古老美德”的追寻,也影响到了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精神分析学说。
非洲之外:迷失的“雅利安人”
“含族假说”在非洲之外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1780年代,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在对梵语、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和凯尔特语进行比较研究后认为,这几种看似不太相关的语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种语言上的相似性,通过与《创世纪》中的记载,以及印度同埃及、波斯等地建筑风格与神话等的相似性结合,威廉·琼斯认为含的后代一开始定居在波斯,但后来有一支向东迁徙进入了印度,而另一支则向西迁徙进入了东地中海和埃及。向西迁徙的一支则在航海技术改进后,开始向北进入欧洲,或是向南进入了非洲内陆。
与此同时,约翰·布卢门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则认为人类起源于高加索山,因为高加索山距离《创世纪》中记载的,大洪水后诺亚方舟停留的亚拉腊山非常近,而高加索人则是“最漂亮的人种”。 布卢门巴赫则通过大量的头骨测量和身体比较,证明高加索人开始向外迁移,一支向东通过波斯迁移到中亚和印度,一支向西迁移到欧洲,而另外一支则进入非洲。随着时间与地理环境的变化,迁移到不同地区的高加索人的外貌也发生了变化,因此产生了不同的人种。因此,布卢门巴赫的理论与威廉·琼斯通过比较语言学得出的结论几乎一致。换言之,布卢门巴赫理论中的“高加索人”,便是威廉·琼斯所言的“含的后代”。
到了19世纪中叶,马科斯·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通过对古代印度,尤其是《梨俱吠陀》的研究,发现古代印度可能存在着一支白皮肤人种入侵征服印度本地深色皮肤土着的历史。在《梨俱吠陀》中,这支白皮肤人种自称为“雅里亚(Ayra)”,意思是“高贵的”、“值得尊敬的”,于是缪勒将其称作“雅利安人(Aryan)”。更进一步,缪勒认为他从《梨俱吠陀》中看到了印度最高贵的种姓——婆罗门的起源:他们有着雅利安人的血统。由此,缪勒认为,浅肤色的人种与深肤色的人种相遇时,后者必将会被前者征服。在缪勒的理论中,他认为“雅利安人”是雅弗的后代。到此,“含族假说”又发生了变化,即开始脱离了《创世纪》的论述,将诺亚的三个孩子合一,又融合了威廉·琼斯开创的比较语言学路径,以及布卢门巴赫的“高加索人迁徙学说”,转变成了“雅利安人入侵理论”。而“雅利安人入侵理论”也开始跳脱了欧、亚、非三大洲的地理限制,覆盖到了全球的范围。
于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前半叶,在世界各地找到异常白人群落的发现不断涌出。例如欧洲传教士在北海道发现了浅肤色、高颧骨、毛发浓密的阿依努人;探险家在北极发现有金色头发,使用铜器的爱斯基摩人;在巴拿马热带丛林里发现白皮肤的印第安人,等等。
然而,随着考古学和遗传生物学的发展,很多此前被认为是“迷失白人”的文明存在被证明是当地文化的前端之作。例如格特鲁德·汤普森(Gertrude Caton Thompson)在对“大津巴布韦”的考古发掘后,认为“大津巴布韦”的建筑形式与中部非洲的波马(Boma)以及南部非洲的牛栏村庄(Kraal)如出一辙。因此这并非是“含的后代”所建筑的,而只是南部非洲的班图先民们的创造。而所谓的白色族群,只不过是一些患有白化病的本地人而已。以此为代表,不论是“含族假说”,还是“雅利安人入侵理论”均开始失去了解释效力。虽然如此,其影响力仍未完全消退,纳粹对西藏的探险考察是这一理论在战前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实践。

大津巴布韦
二战结束后,“含族假说”被进一步证明破产,逐渐消失在了人们的论述中。然而,“含族假说”的阴影并未完全消退。在殖民时代,殖民者们充分利用了这一假说,将肤色较浅的部族扶为高位,而肤色较深的部族则地位较低。待殖民地去殖民化后,浅肤色部族仍旧拥有强烈的优越感,而深肤色部族则对此充满怨恨。由此,大量种族冲突与清洗也由此产生。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尼日利亚的内战,以及卢旺达胡图族针对图西族的种族大屠杀。不仅在非洲,“含族假说”的影响在美国对哥伦布时代之前的历史论述中也存在着影响,如1996年开始对肯纳维克人(Kennewick Man)的争夺。换言之,“含族假说”至今,依旧“阴魂不散”。
探寻白色群落,实则人性使然
在人们开始探求自己未知的事务时,一般会去使用自己熟悉的知识去解释。与其说受制于经典的记录,不如说这是人性的使然。当欧洲人发现存在非洲存在着异常的白人群落时,自然会去思考其与自己有何相似之处。而就欧洲人而言,长期以来最熟悉的知识莫过于《圣经》。因此,“含族假说”在有关人类起源解释上有了一席之地。然而这一席之地,却又给被解释的族群,带来了无尽的苦难。与此同时,“含族假说”的盛行,以及如今的“阴魂不散”,也正是西方世界自工业化时代以来挥之不去的不安全感的体现。以上,便是罗宾森在本书中所呈现的主要内容。
在本书中,罗宾森深入挖掘了一段早已为人忘却,却对人影响至今的历史。同时,罗宾森旁征博引,使用轻快而不失严密的笔法,将欧洲人自上古时代开始对非洲内陆,乃至世界其他地区的白人族群的探索描绘得淋漓尽致。然而,本书的写作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在论及“含族假说”的转变过程时,罗宾森并未提及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的影响。伊迪丝·桑德斯认为,随拿破仑远征进入埃及的学者们在对古代埃及进行研究后认为,古代埃及有着伟大的文明,而创造这种文明的先民们并不像被诅咒的。由此再结合《创世纪》的记载,他们认为古埃及人应该是含没有被诅咒的孩子的后代,而含被诅咒的孩子只有迦南。因此,欧洲人与非洲人的关系,不应是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而是兄弟。而这种认知的转变,为后来的“含族假说”的修正起了催化剂作用(详见Sanders, Edith. 1969. “The Hamatic Hypothesis: Its Origin and Functions in Tim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10, no. 4: 521–32.)。
就“含族假说”本身而言,其作用也并非完全作为将殖民统治合理化的理论基础。在对非洲内陆的探险中,“含族假说”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含族假说”将白种人对深肤色人的统治合理化;另一方面,“含族假说”也与非洲内陆地区的部落传说相结合,成为了非洲内陆部落王国与西方传教势力联结的纽带。在这种基础上,非洲内陆部落王国与沿海的西方势力形成了某种合作关系,即西方势力使用工业品向内陆的部落王国换取奴隶和其他特产。也正因为如此,在非洲内陆殖民化的过程中,以布干达为代表的许多内陆王国依旧保有相当权力。而这些权力的丧失,反而是在去殖民化的过程中。
就去殖民化的过程而言,肤色较浅的部族依旧掌握权力,而肤色较深的部族则依旧地位低下,由此便酿成了去殖民化后的国家内部,殖民时代的政治结构依然存在。然而,经历了去殖民化的过程后,前殖民国家却经历了政治结构颠倒的过程,即较深肤色的部族掌握权力,而较浅肤色的部族地位降低。由此便酿成了新的矛盾。而这种矛盾的产生,毋宁说是“含族假说”的另外一种体现。就这一点而言,罗宾森在书中虽然提到胡图族对图西族的大屠杀也是出于“含族假说”,但就这种去殖民化后政治结构颠倒与“含族假说”的关联,并没有太多描述。此外,书中亦没有提到种族平等理论对“含族假说”逐渐消逝的影响。
在斯坦利与甘巴拉嘎拉山相遇的一百多年后,罗宾森也艰难跋涉到了甘巴拉嘎拉山下。这座热带雪峰在阳光的照耀下依旧像百年前一样耀眼(Gambaragara在当地土语中的意思是“阳光耀眼”)。而斯坦利却从来没有征服过这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山峰(直到1906年,意大利的阿布鲁奇公爵才成功登顶,并将其命名为“斯坦利山(Mount Stanley)”)。就如同他一直心心念念的白色部落,闪烁着光晕,似乎就在那边,却从未到达。

如今的甘巴拉嘎拉山


扫描二维码分享到微信或朋友圈